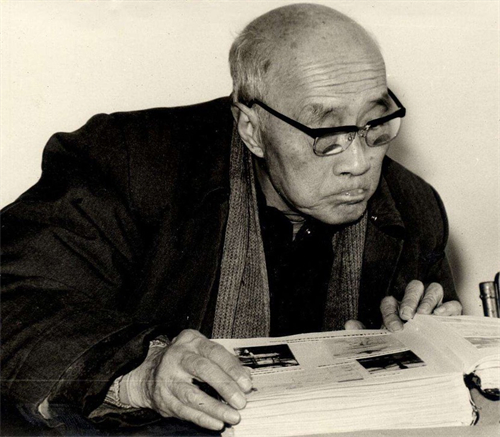
童寯旧照
在所谓“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之事业上,已经靡费了太多骄矜夸耀的话语。如果说,这种复兴仅仅只是给工厂戴上一顶中国庙宇式屋顶的话,那么在一个死人身上加上一条“猪尾巴”便足以使他起死回生!这种做法的早期尝试大多局限在教会的学校和医院上,此类建筑物往往会对(建筑)门外汉们产生一种浪漫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最能体现中国古典建筑之灿烂与辉煌的部分,莫过于那些色彩鲜艳的反曲屋面了。
然而,在建筑师看来,中式屋顶向来都是一种颇为实用的设计手段,便于他施行立面上的“整容”手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他可以先根据每一项现代的要求来安排建筑的内部空间,然后借用一个中国式的屋顶来完成外观形象的设计。
令童寯大为光火的是,某个抓人眼球的符号,或是他眼中“平庸的仿古摆设”,竟然被人们误以为是富有创意的建筑。童寯认为,若要在中国创造一种新类型的建筑,就必须抛弃以往在形式上对双坡出挑屋面的依赖,承认“国际风格”已经“来到并扎根”于中国,进而运用童寯本人从费城的保罗·克瑞那里学到的经验,去开展有质量的设计实践:
无论一座建筑的外观是中式或现代,它的平面只能通过一种方式生成:根据所能获得的最新知识去科学、合理地安排各个房间。因此,立面作为从平面衍生出来的产物,只能是现代主义的。任何试图赋予它地方“特色”的尝试,都需要开展针对性的学习、研究和创新。
童寯在这里论述的,亦是茂飞本人在中国实践二十多年后所学到的经验,即将旧传统融入新建筑之中,或者说将新生命注入一个已经沦为 “纯粹考古学”的建筑传统之中,这至少需要一代人毕生的努力方可有希望达成。
茂飞与梁思成
也许没有任何人的职业生涯比梁思成更能体现这一追求了,他是20世纪唯一一位能与吕彦直媲美的中国建筑师。与其说是一名职业的建筑师,梁思成更像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历史研究者。他毕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启发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和后来众多的追随者。他引导人们重新关注一本重要的建筑论著——北宋官员李诫在公元1103年编撰的《营造法式》,该书的抄本于1920年被发现并重印。他不仅协助创办了东北大学(沈阳)的建筑史课程,还在1931-1937年间,联合其他学者共同主持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该学会成立于1930年,在1930-1937年间出版了一份重要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2月,在营造学会的开幕式上,创始人朱启钤用一段充满希望的话语作为自己演讲的结束语:
“我们越往前走,越觉得中国建筑研究绝非吾人之私产。东方的邻居帮助我们保存下古老的建筑实例,并沿着同样的路线进行了艰苦的研究;西方的朋友为我们提供科学之方法,分享他们在该领域之发现。”
亨利·茂飞是朱启钤所谓营造学社的朋友之一吗?即便是也只是间接的。尽管茂飞与中国营造学社所宣称的目标看似一致,但他并没有见过梁思成本人,也从未以任何方式与营造学社合作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宛如两根置身于同一块布料上的丝线,各自蜿蜒伸展却从未交织在一起。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茂飞更接近于一名商业建筑师,而非一位学术研究者;他将考古学的方法融入对建筑物的精确历史研究之中。写出下述评论的茂飞必然不会得到梁思成较高的评价:
“我本人一直将中国建筑之研究视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放在当下的实际问题中去考量;它并非那些纯粹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激发一些学术圈的兴致与爱好罢了。此外,我必须承认,我对那些机巧的理论全然不感兴趣。例如,试图说明中式屋面的飞檐翘角反映了早期游牧部落帐篷的曲线轮廓,或是舞者旋转飘逸的裙裾等等。我们又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工匠认为弯曲比直线在形式上更为优美之外,仍执著地为反曲屋面寻求更多的解释呢?”
梁思成认为,其目的在于揭示美丽背后的真相。
茂飞对传统做法提出了质疑,
并激发了未来的变革
从同时代中国建筑师对他的评价中可以发现,茂飞并未从许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渐行渐远。除了吕彦直之外,茂飞还是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一些最为杰出之人物的雇主、设计伙伴或美学盟友,他们包括:庄俊、李锦沛、赵深、董大酉、范文照,童寯和杨廷宝。但是,就像无法将这些留美建筑师后来的设计归功于保罗·克瑞或其他任何一位美国建筑学教授一样,说茂飞是激发这些建筑师设计创造力和多样性的唯一源泉,不仅具有误导性,也是不公平的。
此外,茂飞跟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的大部分人物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接触。除了茂飞本人之外,还有陈植、刘敦桢,包括那位最知名的梁思成先生,他们都是“第一代”建筑师中自主开展高质量建筑实践的重要人物。这些人士开展的实践及研究表明,至少在1935年,相对新兴的中国建筑行业已经吸引了大批的专业人才投身其中,并显露出丰富的多元化特征。虽然茂飞早在1928年便曾设想,这样一种“适应性”建筑势必会通过一场“战役”取得胜利,但他却无法预知这场“战役”终将经历多少次的转折与反复, 也难以揣度究竟有多少新生的建筑师会加入这场“战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