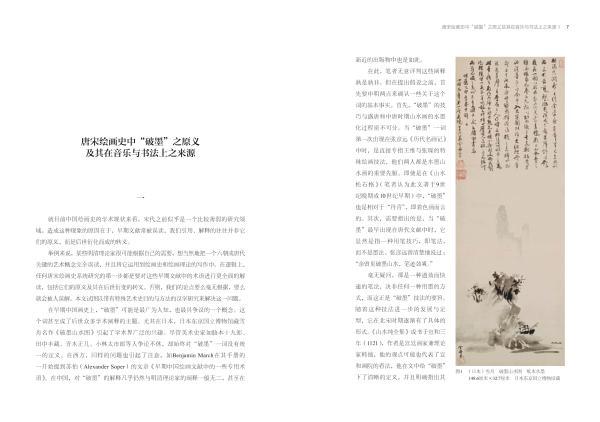
《唐宋绘画史中“破墨”之原义及其在音乐与书法上之来源》,收录于何惠鉴学术著作集《万象自心出:中国古书画研究》
首先,文章厘定了关于“破墨”的两个基本史实。
其一,“破墨”是一种笔法,而非墨法。笔与墨是中国画最主要的两种表现手法,早在荆浩的《笔法记》中,就对“笔”与“墨”做出了宽泛而恰当的定义:“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荆浩品评诸位画家的笔墨特点,认为“李将军理深思远,笔迹甚精,虽巧而华,大亏墨彩”、“吴道子笔胜于象,骨气自高,树不言图,亦恨无墨”、“项容山人树石顽涩,棱角无足追,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可见早期的山水画中,笔与墨堪称殊途,善于用笔的,如李思训、吴道子,在用墨上就有“亏”,有“恨”;而善于用墨的,如项容,在用笔上就没有棱角,缺乏骨力。因此,当时的笔与墨,两种技巧泾渭分明,甚至有所抵牾,还没有能够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山水画初创时期的真实写照。
由此,何惠鉴进一步明确了,“笔”用于描绘轮廓及勾勒衣纹,“墨”以明暗表现形状与纹理。那么,为什么说“破墨”是一种笔法呢?这从张彦远对王维与张璪的描述原文中不难领会,尤其是王维,他记述王维“工画山水,体涉古今。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挥工人布色,原野簇成,远树过于朴拙。复务细巧,翻更失真,清源寺壁上画辋川,笔力雄壮……余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可以想见,王维的山水画,若是着色,多是使工人布色,那么,他主要负责的就是景物形象的塑造,这是“笔法”的表现范围。尽管他的造型有的“朴拙”,有的“细巧”乃至“失真”,但是用笔却是“雄壮”“劲爽”的。由此亦可见,“破墨”隐约是与“着色”,亦即“丹青”相区别的水墨的绘画方式,这种绘画方式与其时寺观壁画的大行其道有很大的关系,也可以与吴道子作画的相关记载互相引证。
其二,“破墨”既然是一种笔法,那么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由张彦远“雄壮”、“劲爽”的措辞来看,它的要旨是快速而强劲。北宋韩拙的《山水纯全集》中对此描述得更加具体,他在《论石》中写道:“夫画石者,贵要磊落雄壮,苍硬顽涩,……皴拂阴阳,点均髙下,乃为破墨之功也”。可见,描绘山石,贵在能表现其“苍硬顽涩”的机理质感,那就要用“破墨”来表现,具体的技巧是“皴拂(分)阴阳,点均高下”,也就是包含了“皴”和“点”两个用笔的要素。
厘清了“破墨”的两个基本史实后,何惠鉴接着开始探究这个词汇的历史源起,这个词在唐代是如何出现的?在最初的文献中,它究竟是怎样一种笔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后世引发出许多歧义的“破”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打破”,还是“被打破”?
接下来的分析与结论出人意料地简单明了、容易理解。
“破”字最初出现在许多音乐评论中,特别是用来描述打击乐中的鼓乐那种急而短的声音。而同时,“破”又是流行于唐宋时代的组曲中的最后一个乐章的名称,通常这种组曲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散序”,舒缓悠扬;第二部分“中序”,节奏开始快起来;最后一部分,音乐越来越急促、欢快、激昂、振奋,直至乐曲结束前达到高潮,即称为“破”或“曲破”,意思是打破之前舒缓、平稳的乐章。所以,“破”字原本是一个专属于音乐评论的词汇,在画论中出现,是被借用的。为什么要借用?因为绘画的成熟晚于音乐,当音乐已经有完整的批评体系的时候,绘画的批评尚未成熟,因此,早期画论中有许多词汇是从音乐,以及同样较早成熟的诗歌当中借用的。
这一步推断可谓神来之笔。阅读古代文献,常会遇到词义不明的情况,即使追根溯源亦无法完全理解其意,此时不但需要扎实的古汉语功底,有时候更可贵的是触类旁通、见微知著的灵感,而这灵感背后,依靠的是深厚的积累、广博的知识以及敏锐的感悟。
“破”字的茅塞一开,后面的论述便顺理成章、势如破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