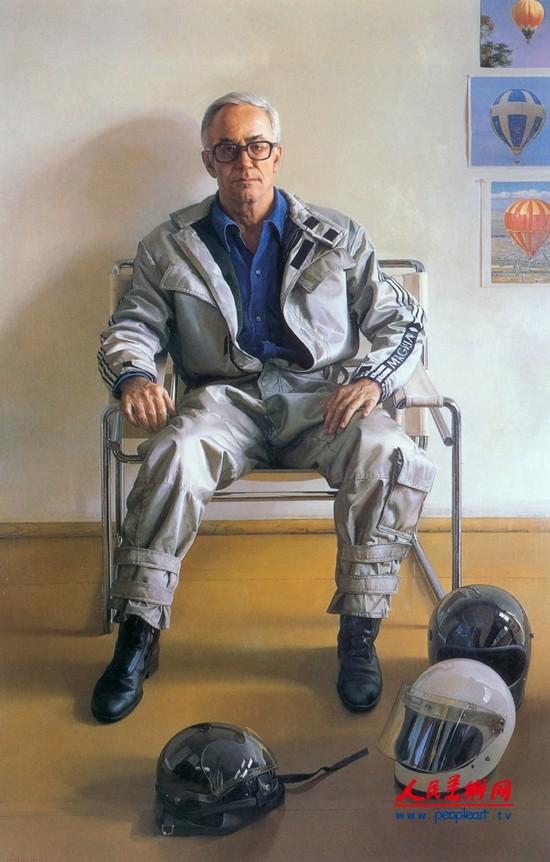
布雷沃的素描与油画风格同貌,精密而概括,丰富内又单纯。简单与复杂并无山海之隔,而细微至极与甜腻却以有一线之差。布雷沃的画,高度精微,却无媚腻之虞,这是最难把握的界限。这正是画家在画面整体感上的高度控制能力,一切精微表现之局部乃至细节决不违背整体概括之大统。整个画面,只有精美的完善,而无刻意求工之嫌,更非逼真及其质感的玄耀,惟有美学的高度及其艺术就力的感甾。如果把布雷沃的作品称作“现实主义”或进一步称作“超现实主义”就如同把水称作岩石、把云称作花岗石一样愚蠢。他的艺术源于传统,是非常令人尊敬的古典传统,但与传统古典画不是联姻,而是独立的现代古典主义,即新古典主义。
布雷沃并非即兴凭灵感的冲动作画,他尽力避免盲目的客观性,且无情地限制复制自然,客观主义与自发性会抵消智慧和想象。画家认为先天的精灵不存在,而是勤奋、思考和想象决定艺术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