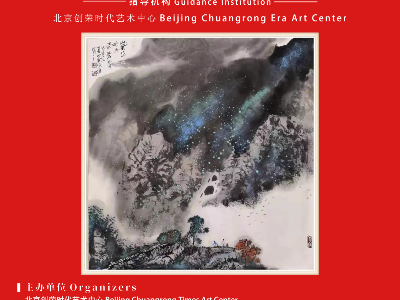科技发展以令人猝不及防的姿态闪亮登场,席卷我们的知识景观,在千千万万的机械重复中,疲劳感随之而来,正在此时,便更彰显出独创性艺术的价值。
纵观青年艺术家苑曾的作品,我们会为其中蕴含的厚重诗意性所吸引,正是这种诗意的精神价值,坚守着艺术作品的灵韵晖光。

苑曾《世界系列》85×65㎝ 油画
苑曾的作品天地开阔,常有不合现实逻辑的高大植物肆意生长,在意象上构成独立的王国,人类则以“沧海一粟”的形象出现,试图去融入画面中的超现实情景。

苑曾 《她在她的世界悄无声息的走》135x90㎝ 油画

苑曾 《风华系列之一》 105x85㎝ 油画
超现实,恰恰最接近现实,苑曾将自我的感受细腻地画出,远不止于客观的物象。正如米兰·昆德拉在其作品中对“诗化记忆”的呈现:人们并非客观地记住过去,而是按照需求、情感和理解来重构过去的记忆,个人经历都可以转化为具有艺术价值的记忆形式。

苑曾作品 《捡时光的假人》76×60㎝ 油画
本期专访,广州国际艺博会与艺术家苑曾展开一场深入的线上对话,围绕创作历程、艺术探索、绘画风格等重点话题,引发关于绘画、个人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思考。

苑曾作品 《世界系列》50×40㎝ 油画
艺术家简介

苑曾(苑保健),当代艺术家,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其作品在艺术展览中受到广泛关注并屡获荣誉,也被多家单位和私人收藏家收藏。
采访
您能分享一下最初是什么激发了您对艺术的兴趣?纵观中外艺术发展史,有无您较为欣赏的艺术大家?他们对您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苑曾:在学艺的最初阶段,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朱刚教授,对我影响十分深远。美术高考的前夕,机缘巧合下我参加了朱刚老师的高考美术培训班。与其它常见的模式化的、应试的美术培训不同,朱刚老师的机构理想化得简直不像个培训机构,他带领我们十几个学生,和他的研究生一起上课。讲什么是畸形的应试化的美术教育现状、什么是正确的艺术方向,经常带我们欣赏分析大师的作品,组织国内有名的艺术家来给我们讲座,培养我们的眼界和正确的艺术审美。在我以后进入美院和毕业后进入社会,见识了艺术界的种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朱刚教授带给我的这些艺术认知的可贵之处。
有价值的艺术是对生活思考的沉淀,是直指心灵的自我表达。帮助我体会这样认知的大师有这几位:法国画家劳特雷克,他是一位艺术的革新者,在当时崇尚精美画风的社会风尚下,他却钟爱于表现红磨坊这一特定底层人群的哀苦和悲戚。其作品中蕴含的深切的人文情感,是我致力于与之共鸣的。
梵高也是我十分钟爱的大师。我的画中会关注身边的普通事物、关注大自然、关注角落的野草和自我的情感世界,从感受出发来作画,就是得益于梵高的启发。
近期我在研究西班牙现实主义画家洛佩兹,他的作品也是以描绘其个人世界为主:生活中的日常物品、亲人、家庭、他所生活的城市街道,他能从这些朴素而平常的事物中敏锐的感受到其蕴含的鲜活生命力,然后以具象写实的手法,极有耐心地将这些感受到的真情实感融入画布中。虽然他采用的是最传统的写实语言,但他的作品却极其富有现代感。这启发我以具象手法进行创作探索时,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写实的语言在当代语境中的意义与可能性。
纵观您的系列作品内容,您的作品常常以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为基础,风格厚重沉郁,并有一种忧伤的诗意感,能否分享一些具体的经历或故事,是如何激发您创作灵感的?
苑曾:是的,我的作品通常是以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为基础,去捕捉和表现这些敏感的瞬间感受。从大的方面来说,它可能是一段时间的生活状态;从小的方面来说,它可能是听了一首歌,看了一部电影一本书,或者只是路过某个路边的普通景物,比如一簇野草,然后产生的瞬间感受。

苑曾《踏刃而起》系列展示效果
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踏刃而起》这个系列,它记录的是对我美院读书期间生活状态的思考和探索的结晶。在美院读书那几年,在学习和未来生活上其实都是处于一种迷茫的困顿状态,前途未卜。但同时又因为年轻人的冲劲,又对未来充满了热情。所以这时产生的创作就是一种矛盾的结合体。
触景生情,在这样的状态下就会有很多自己有感受的元素出现:比如这个系列中经常出现的野草、静默站立的渺小人物、逆光的影子、特别的星云等。技法上我以灰色调为基础,还用了水彩的通透和色粉的厚重朦胧制造反差感结合在纸本上。我希望用这些自然而然出现的元素和技法呈现出生活感受的厚重和忧伤的诗意感。




苑曾《踏刃而起》系列(部分)水彩
同样表现这种生活状态感受的还有作品《那时候我有山一样的体魄 那时候我有波涛汹涌的豪情》,这幅作品除了一幅油画创作,还有一幅等大的素描。我计划后期慢慢把它发展成一个系列。它也是一段时间生活感受的体会和表达。画面中的元素有旷野、迟暮老人,但同时也有一种挑战的姿势和留存的激情,它也是一种矛盾的结合体。


苑曾《那时候我有山一样的体魄 那时候我有波涛汹涌的豪情》
上:油画稿,下:素描稿
《阿诗玛》则以从小的瞬间感受为出发创作。当时听左小祖咒的一首《恩惠》中的歌词:“阿丝玛背着她的长子抱着她的幼子,走在塔克拉玛干”,歌词触发了我的联想,给我一种悲天悯人的触动。所以这种类型的画是感动瞬间的记录和表达吧。

苑曾《阿诗玛》138×90㎝ 油画
《九月》也是这种瞬间感受类型的创作。我在画这幅的时候很注重现场的写生感,因为它表达的就是我当时路过这个现场时的一种综合感受。画中这些在建设中的蓝色楼房,是我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路上都会反复看到的一个场景。它们沐浴在早晨的薄雾和特定的光线氛围里,让我产生了一种诗意感,很像海子的《九月》这首诗。它还有一种现实物体的鲜活精神性,让我有了延展开来的思考,我也会同时跟几个意向联系起来,比如向日葵、行人、野草,最后这些元素在画中综合起来来呈现我的感受和思考。

苑曾《九月》 80×100㎝ 油画
您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不合现实逻辑的高大植物和渺小的人物形象,您如何看待超现实主义对您创作的影响?在创作超现实场景时,您是如何平衡内心感受与现实世界的呈现的?可否与我们分享下形成此艺术风格的探索过程?
苑曾: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具体属于什么风格。我在作品中刻画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感受,实质是想表达主观的内心情怀。这种主观感受又是因为一些客观的物体去激发产生的,它是赋予这些客观物象之上的精神性寓意。之所以形成超现实主义风格,只是因为它恰好能兼容我的主观感受和客观存在。这种隐含幻象的超现实绘画,是我回应现实的一种方式。

苑曾 《那时候》 90x80㎝ 水彩
比如我看到一簇野草从时,常常感觉其间存在一个宏大的世界,蕴藏着无限生机,植物的血液在躯体内潺潺流动,它的周遭空气流动,光影流转,有一个微小又宏大的世界在运行,就像佛家所说的:“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我直接描绘这些景物本身和周遭的空气、光线,但我希望情绪能在我描绘的对象中浮现。这些情绪是我在生活中,或者是音乐、电影、书籍中的感受,可能是忧伤、欢喜、别离亦或是美好的种种。我希望赋予这些野草以精神性,通过野草这种客观物象去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主观感受。所以,我在追求刻画的不是这些物象本身,而是这些物象背后的寓意,是它内在的一种大自然本质。如果在画面中把它与自己的心境联系起来,就是一种人与自然交互运动的超现实表达。

苑曾《往世系列》60×40㎝ 油画
另外我觉得如果艺术家在创作时,先预设了自己的创作风格,然后再去找相应的内容去往里面填充,这个顺序可能就反了。应该是先产生内容,风格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至于画什么内容,我觉得不是在画面上去闭门造车地探索,反而是画画之外的生活积淀慢慢形成的创作内容,这种积淀,漫长的比如自己的生活经历,短暂的比如读的书和听的音乐。像我对植物的表达,主要跟我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产生的对植物的依赖和寄托有关。创作内容也是遵循从内心出发的原则,这也是那些真正有艺术价值的大师们的作品给我们的共同启示。
总的来说,我不想具体停留在某一种风格上,我希望随着我对创作内容的思考和探索,风格会继续演化。
您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平衡个人风格与时代精神?在您看来,艺术家在当代社会中应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或责任?
苑曾:我所从事的这种具象类的绘画风格,深知不是这个艺术环境的主流。现在这个艺术大环境充斥着矫揉造作的噱头或者甜腻的技巧展示。我觉得应对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坚持自我的表达,不能随波逐流,我希望做有深度、有厚重感的艺术。
艺术家要承担的角色和社会责任,我觉得蛮重要的,尤其是在当下这种浮躁的大环境里,人们在金钱和娱乐主义里奔忙。一个好的艺术家的作品应该是对当下时代的反应还有剖析,可以引导人们有一些自省和思考。好的艺术家要为这个时代的优秀情感负责。
艺术家的作品可以深刻的介入社会生活,是对社会和自我感受的反应,所以不能麻木,不能只是阳春白雪,应该用画笔保持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如鲁迅一般,对环境进行剖析和改造,如果改造不了环境,那就用画笔剖析自我,展现自我感受到的精神世界。
您未来的艺术计划和创作方向是什么?您有没有计划尝试新的艺术形式或探索新的艺术主题?最后,您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或观点?
苑曾:我接下来想尝试和抽象相结合,就是一种“新具象”,它将能更好地兼容我的想法。
还有一批已构思了草图的作品正等待完成,另外我还计划完成一批探讨架上绘画与电影影像之间关系的绘画作品。

苑曾《往世系列》60×40㎝ 油画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关于艺术教育的感悟。我在画画创作之余,还在从事艺术教育,深刻体会到人们对于正确艺术认知的缺乏,大部分的认知还处在只有看得懂的、像的、好看的才是画画,比如自己的孩子如果完成了一幅有自我表达的画面,大部分人内心会觉得画的幼稚、看不懂、不好看也不专业。很多孩子被大人和艺术教育大环境塑造成了画画是为了画面效果,为了“愉悦大人”的模式画的样子,享受不到表达自我的高级乐趣,这很危险。艺术家应该有责任去引领这些,让孩子有能力在未来用艺术的手段对世界进行独立思考,有能力去探索追逐精神世界,而不是止步于对物质世界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