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书本、身体,构成了阅读的基本要素,三者之间的关系简单而有趣:世界存在于书本,书本被身体掌握,身体又处在世界的某一处。就像人们自由选择自己的读本一样,人们更有权利选择自己阅读的姿态。这说起来是很私性,平常甚至不会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但在反映阅读情形的艺术作品那里,它确实又有些微言大意:阅读定格了那些时空的主人和他们的年代,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阅读是为了活着”。绘画证明曾经有过这样的活法,12种阅读的姿态就是其抽样。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内部来组合文字的隐喻,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面相、环境以及氛围的具体图像还原已有的经验,甚至揣度书本那些看不见的内容,辨认和遥想这些残片的意义,俾以了解自身与自处。

不知为什么,庞贝壁画中表现的日常生活总是让我叹息,世俗美意,千姿万态,最终不敌瞬间一劫,化为灰烬。对于那些传说中的女卜者来说,她们到底能预言什么呢?这个握笔执书的女人也许能以诗艺知会将要到来的毁灭,但神的旨意让她暂时做一位密使,此刻唯有选择守口如瓶。

读书的玛利亚,圣画中屡见的题材。和普通的读书不同,这是一种信仰——玛利亚明白,她与她儿子的一生事件已经在诸经书中有所预言,她就是“智慧”的母亲,教化他人的心灵。韦登是早期尼德兰美术的伟大巨匠之一,这个地区的画家坦率地感应周围的的世界,即使是宗教题材,也充满世俗的真切感受,例如玛利亚用布小心地用布包着宗教手抄本,唯恐书受到损害,因为在韦登的时代,书籍是贵重物品,拥有书籍也是一种特权。她的虔诚表明了归属感,当然也为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圣子基督的形象是一种写在处女肌肤上的书??由圣父安排,写在受孕的母亲身上,由诞生的宣示而阐明。”(杰西·盖尔里希《中世纪书的观念》)
书籍需要在它的内容和阅读的环境之间有一个正比,尤其当绘画无法显露书意的时候,阅读的场所往往决定了书籍的性格。古代中国人喜欢在庭院或山水中寄情于阅读,清风袭人,相看不厌,就像这幅画所描绘的那样,菊香、薰香、茶香烘托了书香,一种似真似幻的人间仙境,这样的阅读实在是雅致得奢侈。陈洪绶的许多作品反映了文人淑女的读书乐趣,他的细节处理高古奇拙,有时不免有故弄玄虚之感,但如果借物以暗示书中内容的涉笔有险或跌宕起伏,倒是合适不过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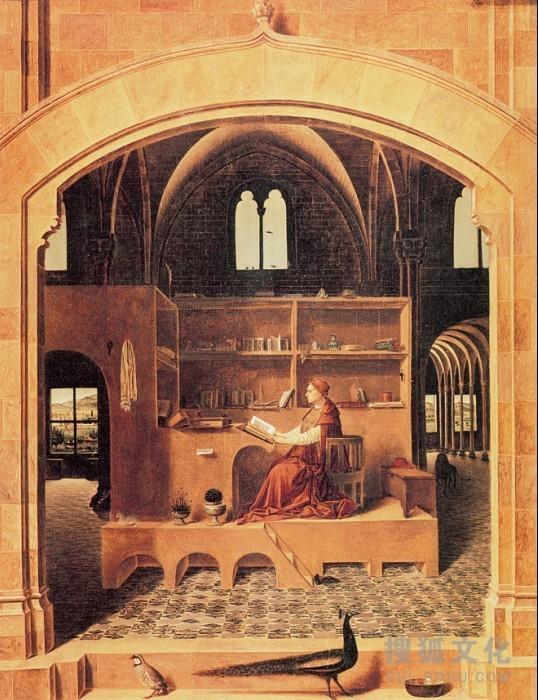
阅读给人以独处的借口,但如此这般眩耀独处实在不多见,因此读书一旦变成仪式,就离真正的阅读相去甚远。当然,书本不能替代真正的世界,万事万物皆是媒介,世界的原理既隐藏在字里行间,也隐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就像戏剧舞台上布满了种种符号,等待感官和智识去辨认、梳理、定义,“而我就是国王/蜜蜂来我身旁歌颂/燕子为我飞翔”。(斯蒂文生)

就像我们可以通过霍尔拜因、凡·代克的绘画了解亨利八世、查尔斯一世的宫廷,布龙吉诺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宫廷的样式--16世纪意大利宫廷中深受欢迎的矫饰主义风格。这幅文学家拉瓦拉·巴提斐利的肖像就相当“装模作样”,布龙吉诺曾经在一首诗歌中形容这位女性朋友“内侧是铁,外侧是冰”,而在画面中,他却意味深长地将之塑造成“侧面是脸,正面是书”,这是为了显示不凡还是为了揭示辩证?也许,同时具有文学天赋的布龙吉诺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无论怎样奇装异裹,半遮半掩的面孔只是生命的冰山一角,而书与文字,才是安身立命的坦荡之物。

普鲁斯特认为,读书是“需有一种不可亵渎的孤独才能进行的活动:阅读,幻想,悲伤与感官的愉悦”,但对于这幅《蓬皮杜夫人》来说,她的满足感似乎不在阅读时的自闭,反而有一种翘首以待的神情,正为其他什么更向往的事情所牵挂。书虽然拿在手上,但时刻准备滑落--她无力把握虚幻之词。也许在那个年代,“书”,就是浮华品味的小道具,装饰奢靡的小花边,雕刻洛可可时光的小翻卷,这对洛可可时期的宫廷画师布歇来说,摆设这样的姿态,不过是游刃有余的小伎俩。

这是一个春天的故事。对有情人来说,燕寝怡情已经够让人销魂的了,何况还有“秘戏图册”聊以遣兴?中国的春宫画并不像日本的春宫画那么感官化,和许多艳词一样,它花了过多的笔墨描绘周遭的环境,节令的景致其实暗合了所谓的春情,天人合一,如同这幅画面所描绘的那样。因此,清秀的男子和缠绵的女子共读“春册”并没有意想中的淫猥之感,而是风和日丽,琴瑟相和,一种坦然的生机呼之欲出。

1888年,三十五岁的凡·高离开巴黎移居阿尔,法国南部的阳光使他伤痛的心灵得到慰藉,创作了不少作品。这幅《阿尔之妇女吉努夫人》画的是在车站前经营咖啡馆的吉努夫人,据说是凡·高趁与他同住的画家高更正在说服她作模特儿时迅速完成的作品,吉努夫人显然受到打搅,目光游离,那本摊开的书不再为她所读。我们熟悉类似的恍惚,在阅读的过程中,那字里行间的打盹是旅程中的逗号,即使我们知道生命结尾的意外或不意外是无可抗拒的,这也是值得回味的出窍之时,就像凡·高此刻享受了一个平和的下午时光是多么地难得。

如今谁都能享受读书之乐,但在《读书的少女》完成时的18世纪,文盲比率相当高,只有受教于家庭教师的上流社会的绅士名媛,才可以体会到阅读的愉悦,因此,书本、家具、服装的引用,也就不是简单的物品功能,它具有一种象征功能,那就是社会地位的眩耀,描绘一幅传世的画像更是如此。不过,作为18世纪法国绚烂豪华的贵族文化盛期的代表画家福拉哥纳尔,倒是在这里优先表达了生活的娴静,华丽暂时被知性的光晕环罩。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手捧的一定不是圣经,而是当时刚刚兴起的流行读物“小说”,从1740年到1760年短短二十年间,大约有一千册小说面世,其中大多是恋爱小说,这对于悠闲富足的闺中少女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春药。

比亚兹莱是个插图家吗?似是而非,因为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并不将自己的创造囿于依附的文字或书刊,他有顽强的个人基因,像罂粟一样复制传播自己酿造的毒。19世纪末文艺天空弥漫着一股'恶之花'的味道,他们以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作为挑战对象,比亚兹莱就是绘画的代表,“不安的,好考究的,傲慢的情调”(鲁迅)。这幅海报一如他的惯常风格,极为简单的曲线,精心雕琢的构图,黑白棕三种颜色的对比,一个妖媚的母亲手捧读本。不过,以这样怪诞的肉欲之身与“孩子”和“书”联系起来,这实在是太离谱了,难怪鲁迅对他有这样的赞叹,“比亚兹莱是个讽刺家,他只能如Baudelaire描写地狱,没有指出一点现代的天堂底反映。这是因为他爱美而美的堕落才困制他;这是因为他如此极端地自觉美德而败德才有取得之理由。有时他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底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

是否一睁开眼,或者一旦打开面前的书,世界就会完全不一样?双重闭合意味着暂时的安宁,但并不是说没有恐惧,因为它们过于对峙了,害怕被另一种力量闯入,唯有沉默和漠然可以维护此间的平衡。契里柯的画总是营造了阴郁的气氛,充满不解之谜。人们习惯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解释其中的秘密,一种说法是画作表现了艺术家对父亲的恐惧,另一种说法以恋母情结为依据,将“书籍”视为艺术家的母亲,并给予露出的“书签”赋予性的含义,但无论如何,这本书的作用不言而喻,它是举足轻重的象征物,“自由被影响的样板/因为命运的存在/它把我们抓住/巨大多余的外界跟我们自己等和”。(里尔克)
在巴尔蒂斯笔下,女孩们读书、照镜、玩牌,这些私密的行为和外部世界脱离了干系,自我专注于轻蔑的欢快。其实,行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行使行为的身体语言,总带有反抗禁忌事物的刺激味道--没有一个阅读的姿态像她们这样别扭,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如果这算得上是一种调皮的话,那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在色欲与无耻怠惰的畛域里,诱引和献身是一道青春期的算术题,而我们的所有解答都不正确,永远陷入绘画的“洛丽塔猜想”不能自拨。这些发生在房间里的故事是虚假,是诡计,是圈套,是谜,它存心使看得见的世界乃至书本存在,但又全然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