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诗意的限度
——评电影《王的盛宴》
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而言,诗意不应与真实相抵牾,也不应与伦理背道而驰。美并不是绝对可以无视真和善的存在。今天,绝大多数普通电影消费者对历史的认知是模糊的,对道德的理解是多元的,包括主流电影在内主流文化更应承担起传播准确信息、传达正面价值观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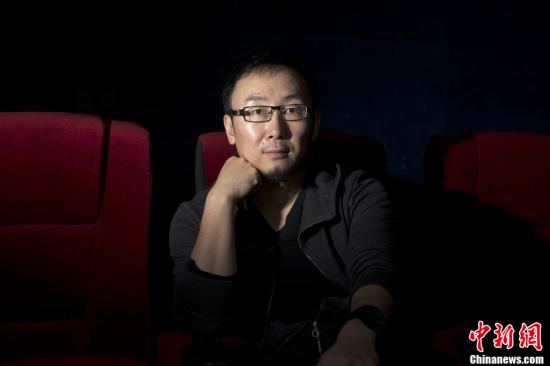
陆川
档期多次延后的影片《王的盛宴》(下称《盛宴》)日前终于公诸观众面前。从目前的市场反应看,可称平平。考虑到同时期的大片均为知名导演作品,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不过在影评空间里,特别是在网络影评平台上,各种批评一直围绕着《盛宴》和陆川,措辞激烈,穷追猛打,这倒令人不得不仔细琢磨何以如此了。

《王的盛宴》主创
平心而论,在近年数量众多的国产片里,《盛宴》的视听语言当属上乘。用刘邦的意识流穿起数十年间的王图霸业、多少豪杰,构思可谓精巧,流畅的剪辑也帮助这一意图得以较好的实现。用影像复现城邦、山野、战场、营寨,大都经得起盘问(大水包围的秦王宫除外)。笔者认为,影片最出彩的环节仍在光影、色彩和摄影。至于舞美道具,陆川更是花了许多心思。虽然也能看出用力过度的痕迹和经典古装战争片(如黑泽明《乱》)的影子,但总体上看,仍达到了相当理想的视听效果。
至于陆川的创作诚意,也应该得到承认。从他的访谈和公共场合表现,更主要从他作品对人物内心情感的表达来看,陆川性情中人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肯定这两方面之后,有关《盛宴》的争议就集中到内容和主题层面了。
一是关于真实。在历史问题上,陆川向来喜欢做翻案文章,《盛宴》亦然。影片开头字幕表示,本片是根据司马迁《史记》而作,但实际上却近乎全盘颠覆。从历史片创作的模式和标准来看,李仁港的《鸿门宴传奇》不会招致责难,因为其原本定位就是演义。既然《盛宴》定位在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和重述上,那么就惟有接受更严格的拷问,无可逃避。质疑古史的出发点没有问题,重写历史的落脚点则必须有足够的史实考证。陆川的做法是:发现《史记》中若干细节今人难以索解,于是全盘否定其可能性,进而提出自己的假说,并敷衍成新的一家之言。
在《史记》中,刘邦是一位结合了野心、勇气、智谋、无赖、乐观的草莽帝王,这种气质与他那首传世的《大风歌》相吻合。在影片里,刘邦更像是一个被恐惧折磨、无比忧郁纠结的文人,古怪地结合了精神病人和存在主义者的双重特质。而之所以如此,似乎仅仅因为鸿门宴的惊吓后遗症、以及惟恐被臣下夺去天下的受迫害狂。《盛宴》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想象莫过于假设鸿门宴上项羽参与主动放走了刘邦,给出的理由仅仅是项羽为人很高尚。这样的翻案未免太过主观臆断,近乎儿戏。当然,他可以辩称自己只是在拍电影、艺术虚构而已,但若果真如此,又何必作出与司马迁大辩论一番的姿态?对于那些读过高祖、项羽两本纪的观众,司马迁的人物明显要更丰满、事件陈述更可信。如果《史记》的历史叙述有问题,《盛宴》的问题岂非更大?
二是关于道德。《盛宴》中,吕后貌似雄辩地论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大前提),项羽高尚(小前提),项羽惨死(结论),因此我们必须放弃高尚,并杀死所有威胁我们的人(推论)。这个谬误到离奇的逻辑同样是肤浅存在主义者喜好的,而在影片中居然说服了汉代名臣张良萧何,把他二人拖进人性恶的深渊,更拖进逻辑自我循环的怪圈。与此同时,韩信成为羔羊,再次去验证大前提的正确。但在“为什么是韩信成为羔羊”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找不到充足的理由。惟一确定的是,当我们试图跟上这种逻辑的时候,我们的道德观不知不觉在瓦解。如果作品的所谓深刻只是人性恶命题,那么除了耸人听闻以外,真的无法站住脚。因为性善性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统计上,无疑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从来不可能只存在一种。
再进一步看,人性论是哲学、伦理学命题,用以解答和理解历史远远不够。历史学界早已指出,战国末期的生产方式变化、经济规模扩大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结构正走向大一统,楚汉相争的背后是周制和秦制的对立,后者必然取代前者。当然,这样的学术论说无助于故事的精彩,但如果主创者认识到此地步,应该可以有助于跳出惟人性论的缥缈狭隘。
现在,惺惺作态的历史战争加动作大片终于难以为继,光怪陆离的国产古装电视剧仍然肆虐着观众眼球。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任何认真、有诚意的历史片创作都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但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历史片创作有诚意、做一番功课就够了。对于主流电影来说,科学的历史观和正确的伦理观仍然是基础。就《盛宴》而言,如前所说,我们不能抹杀陆川所下的功夫,包括历史探索、哲理思考和诗意表达。从影片高度风格化的视听语言来看,诗意又超过了史事和哲思。但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而言,诗意不应与真实相抵牾,也不应与伦理背道而驰。美并不是绝对可以无视真和善的存在。今天,绝大多数普通电影消费者对历史的认知是模糊的,对道德的理解是多元的,包括主流电影在内主流文化更应承担起传播准确信息、传达正面价值观的任务。真、善、美的统一如何可能,这个极其古老的论题,在我们现实生存和思考领域仍在角力。
认清这些并不是太难的工作,关键是要意识到:不能为了推翻古史的快感、个人叙事的快感、批判人性的快感等有意无意地遮蔽历史和伦理。在忧郁纠结的存在主义者萨特之后,为了不被各种话语蒙蔽,法国学者福柯认为,知识分子需要不屈不挠的博学;而心理学家拉康补充说,蒙蔽人的正是人的自恋。好学如陆川,不妨听听这二位的声音。否则,即便成功雕琢出形式的美感,也难以赎买历史观的空洞和伦理观的虚无。而且,在福柯和拉康看来,这样的快感其实源于自我话语权确立的幻觉之上。从诗意的幻觉走向话语权的幻觉,在推翻权威或主流的历史观价值观之后,把自己的观念退给观众,是陆川一直以来的冲动。有趣的是,这种“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心理倒恰恰和项羽对秦始皇的态度如出一辙。影片中浪漫、高贵、诗意的项羽,不知道是否是陆川在潜意识层面的自我认同。
在幻觉被知性唤醒之前,作为思考者(或者力图成为思考者),陆川还很难宣称自己是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