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摄影家安德里亚斯·古尔斯基的作品《99美分II》在苏富比艺术品专场拍卖中以334.6万美元成交,创下了当时摄影作品拍卖价格全球新高。
摄影作品的收藏进入艺术品市场仅十几年,所有油画、雕塑、书画、瓷器等等司空见惯的艺术收藏门类所遇见的问题概莫能外。2012上海国际摄影展以收藏为主题的论坛上透露出的信息显示,年轻而具有独立判断力的藏家,成为摄影收藏的希望所在,上海因为站在中国的最前面,而成为这项新兴收藏项目最可能生长壮大的地方。
出现在世贸商城举行的2012上海国际摄影展摄影收藏论坛主席台上的方喻,生于1983年,名片上的头衔已然是一家网络科技公司的创始人。语速缓和,审慎有度,圆脸戴眼镜的他,其形象俨然十分符合摄影作品市场针对的理想收藏群体的设想:年轻——意味着对艺术作品的口味更趋向先锋前卫,宽容度更高;多金——但又非传统意义上“腰缠万贯”的老板。自2010年始投身摄影收藏的行列,方喻已经拥有的藏品并不算多,20-30张,却成为系列,绝大部分是1930年之前的老照片。除此之外,方喻还有一个长达20年的摄影收藏计划,如果按照方喻的理想得以推进,他将会在2030年举办一个专题展览。
没有刻意定下的功利性目标,只是为照片本身所蕴含的人文价值所撼动,这本该是推动一切艺术收藏的动力,在人人一心一意关切“涨幅可达多少”的当下,却尤显珍贵。
摄影究竟是不是门艺术的争论自摄影诞生之时起便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一并向前,但摄影作品的收藏进入艺术品市场仅仅十几年,所有油画、雕塑、书画、瓷器等等司空见惯的艺术收藏门类所遇见的问题概莫能外。
拍卖行的公开拍卖成交纪录成为摄影收藏正在兴起的一个标准,摄影收藏拍卖中拔得头筹的摄影作品,其中一幅是2006年2月纽约苏富比拍出的当时最贵照片——美国摄影家爱德华·斯泰肯(1879-1973)1904年摄于长岛的《池塘月光》:292万美元,而这幅作品的最原始销售记录只有75美元。一年后的7月,德国摄影家安德里亚斯·古尔斯基的作品《99美分II》在苏富比艺术品专场拍卖中以334.6万美元成交,也创下了当时摄影作品拍卖价格全球新高。而几个月后的同年11月,理查德·普林斯的《牛仔》则以340万美元的价格又刷新了纪录。2008年6月,虽然金融危机阴霾还未散去,纽约苏富比拍卖由20世纪一些最知名摄影大师,包括安瑟·亚当斯(AnselAdam)、大卫·贝利(DavidBailey)等阵容组成的“摄影大师宝丽来作品”,1260幅宝丽来软片与银盐相纸作品,拍卖总成交额达到1200万美元。2011年的11月13日,上世纪著名影星周璇个人珍存的近2000张原版老照片在北京华辰拍卖,结果以218.5万元成交,创出国内影像拍卖市场单个标的价格新高。
老外收藏当代
国人偏爱老照片
尚不到而立之年的方喻从小学习绘画,爱好摄影理所当然,家族里的长辈收藏玉器、书画,让他具备了一定的艺术背景、鉴赏力,以及独立的艺术判断。2010年,在同龄人对于余钱的处理方式尚停留在买车买房之际,方喻开始涉足收藏摄影。起因并不复杂——一些相关的报道使之关注到在国内市场尚未真正热起来的摄影作品收藏领域。
“相比较其他艺术收藏,诸如油画、书画、瓷器,市场在短期内如此火爆,炒作的痕迹过于深重,而摄影,相对来说显得安静些。”他出手收下的第一批照片,便是从华辰的春拍中买下的威廉·桑德斯作品,19世纪末在上海开办照相馆的威廉·桑德斯镜头下的中国人肖像打动了方喻,“其中透露出当时的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品相佳,艺术家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这些因素构成了方喻以2万多元人民币的代价买入作品的最主要动机。此番契机,使1930年之前的老照片成为了方喻目前主要的收藏方向。按照他的理想计划,每年对于自己的收藏投入在5万-10万元人民币之间,以此为代价收藏十几张二十几张1930年前的老照片。方喻把这项收藏计划做到了20年之后,那时候,也就是2030年,与1930年的距离恰好是百年,从自己的收藏出发,便可以做一个相关主题的展览。
方喻的周围自然形成有一个收藏老照片的群体,其中以中国人为多,而收藏中国当代摄影的,则绝大部分是海外藏家,这个分类也基本代表了目前中国国内可以看到的摄影收藏群体的大致趋向。
北京798艺术区内最早从事影像买卖行业的百年印象艺术总监陈光俊在2012年的上海国际摄影展论坛上指出,当代影像在百年印象的成交量中所占到的比例远大于传统影像,近两年尤其如此,当代影像销售甚至占到画廊销售的90%。
为什么传统意义上体现摄影价值注重记录时间事件的“DOCUMENTRY即纪实摄影”缺乏市场青睐?陈光俊认为,主要是由于摄影作品的买家绝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对这些国外藏家而言,要了解一幅中国纪实摄影作品的价值所在,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具备太多的人文背景、历史脉络的了解,语言文化所构成的理解障碍横亘其中,而以当代艺术为创作手段的当代摄影的叙事方法、表达方式,与世界同步,并不看重瞬间,而是强调主观的呈现方式。“90%的藏家来自国外,他们只关注他们能够看懂的东西。”上海全摄影画廊艺术总监黄云鹤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但是黄云鹤给出的数据是顾客中有30%的中国人。
有“影像魔术师”之称的摄影师杰利·尤斯曼曾说过:“据我所知,在国外有很多著名的摄影收藏家,他们偏爱收藏中国的摄影作品。因为中国复杂多变的天气、变幻莫测的地形,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丰富多彩、富于变化。”不需要讲太多深奥注释的表面化表达,东方奇情录般的画面,是西方藏家好奇心所致的收藏趋向。

依此原则,国内藏家趋向于老照片的收藏不足为怪,那些因为岁月而凝结在影像上的痕迹,随时间流逝而带来的色彩的变化,微微的泛黄褪色,本身凸显的便是一种来自历史的魅力。而与此类似于本能的收藏冲动的比较之下,介入中国当代摄影,显然后天的培养和教育环境更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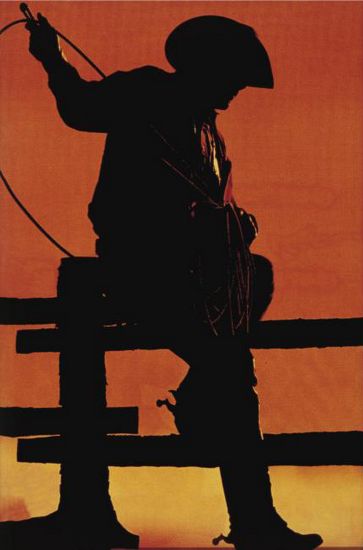
理查德·普林斯的《牛仔》以34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中国最早从事摄影作品经营的亦安画廊屡屡被业内提及,在上海经营多年之后,亦安画廊搬去了北京798园区,其负责人张明放最初介入摄影收藏的目的多也出自内心的喜爱。他认为,对摄影不了解的人,不会对摄影史进行研究,因此,摄影的市场十分狭小,“很多人喜欢买摄影器材,花费几十万买器材毫不心疼,但他们不会去买作品收藏。”亦安画廊的顾客,以前是外国人,现在顾客中80%是艺术家,艺术家的购买行为出于创作需要,一般观众很少买。“人们的心目中尚未形成一个对于摄影作品好坏与否的评判标准,如果美术馆博物馆里能有一个空间专门展示摄影,让观众直面摄影原作,而不是从画册复制品中体味到摄影的魅力,这样可能会有利于潜在藏家的培养。”

爱德华·斯泰肯1904年作品《池塘月光》拍出292万美元。
市场价值并不等同于学术价值
影像作品收藏价值的判定,中国影像独立专场拍卖会创始人、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影像部经理李欣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判断标准:首先看影像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艺术性越高,市场价值也就越高;第二要看是不是名家名作;第三看是否具有文化和历史价值;最后再看影像作品的品相如何。对于老照片的收藏,李欣认为应要收藏对社会和历史有意义,记录了某段历史或者社会发展的老照片。不同于李欣,年轻的画廊经营者黄云鹤因为更多经营当代观念摄影而产生了不同的评判标准,他认为,首要的艺术价值之外,还要有摄影观念,语言的运用以及“学术经历”——即摄影作品背后有无完整的美术馆收藏。“市场价值与学术价值并不完全等同。”
李欣建议刚开始关注影像收藏的藏家,应该选择可靠的渠道入手,不要从摄影师手中直接购买作品。就前面提到的方喻,他最初的收藏从华辰拍卖开始。但是,相对于二级市场的复杂性,更多的摄影师并不是通过拍卖行销售自己的作品,他们与画廊和藏家的关系更为紧密。方喻也承认,自己和摄影师马良的关系十分密切。同时,方喻身边一群藏友也会定期互相转赠交换藏品。
陈光俊认为,影像靠科技进步仍然会有一定的创作空间。因为科技进步,遗留下来的那些打上过去烙印的旧式制作方法,渐渐消亡而变得稀少,显出其珍贵。这是由于科技发展带来的悖论。
“限量”:摄影收藏的疑问
摄影作品具有的复制性易于广泛传播,而一般收藏的价值在于其稀有性,“物以稀为贵”,所以限量的复制是摄影师必须严格遵循的游戏规则和共识。
“作品限量”是指某作品的最多销售数量。当收藏者一拿到一件摄影作品,首先就要关注作品的限售量和尺寸。作为藏品的摄影作品,除了作者的签名以外,还要标明每一幅作品的限售量和编号。而摄影师一般会把这幅作品的限量和每张作品的限量编号写在作品或作品的装裱板上。如限量5张,指同一尺寸的最多制作和销售量为5张。一般来讲,同一作品,作品的限售量越低,尺寸越大,价钱就越高。在2004年,摄影师谢海龙藉此成名的作品《希望工程之大眼睛》总共有30张,第一张的售价只有600美元。此后,这幅照片在各种摄影展上陆续卖出23张,随着所剩数量的减少,该作品也在不断升值。
纽约珍妮特·博登有限公司的画廊经营者珍妮特·博登(JanetBorden)说:“限量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收藏实际上是为了拥有一件十分稀有,甚至仅有的物品。收藏者所要的不仅是原创的概念,而且包括了可以触摸的特殊物件。限量,通常是较小的数量,这成为维系当今收藏市场的生命线。限量有时甚至会成为令客户采取行动的唯一动力。”
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开普拉泽欧(Cappellazzo)说:“(摄影收藏市场)有一个强大的信誉体制,我毫不担心有人违规。”她相信她知道摄影师们如何决定他们的作品限量。她对实力派摄影师提出的建议是:“保持较少的限量,使它成为珍品。”
“在国外,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成熟的资本主义商业市场让买卖双方彼此达成共识,但是在国内,却常常遭到这样的疑问。”陈光俊说,往往,年轻的摄影师更理解规则的含义,因为他们明白,违背诚信的代价是惨痛的,“怎么在这个行业当中混下去啊?”反倒是年长的摄影师对此规则视若无睹,或者偷偷行事。“人品”和“艺品”的合作两大标准里,显然,“人品”首当其冲。
“量太大”是自2008年中国当代摄影市场经过一年的红火之后一蹶不振的一大理由。
有位红极一时的观念摄影师,其作品是将宋徽宗的传统绘画元素以现代元素比如一只在脖子上被抹了一刀而倒地的死鸟置换掉。同一张底片上的影像,在这位摄影师手中,大中小的尺寸各放12张,假设市场价一张卖3000美元,如是炮制一张底片便可以卖出100多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而以同样的百万元价格在艺术市场内可买到不错的名家书画,孰轻孰重,昭然若揭。但是,摄影师依然觉得不够,同样场景,换个角度再拍一遍,等同于变相复制,复制版数又多出了一倍,价格怎能不受此影响?本也只是试水摄影作品收藏领域的藏家,看到这个架势,更是缩回了收藏的念头。
限量的游戏规则,本应出自法律和道德对摄影师的制约,但现在,仅仅存在于自身利益对于摄影师的制约。
摄影收藏的终极目标
就像其他领域的收藏一样,专事摄影收藏的人也经常会被问及及自问:“上涨的空间有多少?借此收益的可能有多大?”几乎没有人会涉及摄影作品中蕴藏的文化内涵、历史信息、人文价值,作为艺术品收藏的种类,未免有些可怜。
长期致力于摄影作品收藏的比极艺术中心总监尚陆则对中国摄影“市场”二字充满了怀疑和不解:“中国的影像市场不正常,不成熟。在国外,一开始都是图书馆或者博物馆做影像展览和收藏,而在中国是靠拍卖,在拍卖市场上转来转去与喜爱摄影作品的收藏不是一回事。中国的摄影收藏心态就像是在搞房地产、搞股票,要翻几番,定这个价值的是拍卖行而不是画廊、收藏家或者艺术家,也不是美术馆、博物馆。”尚陆的顾客中基本没有中国人,“我的顾客收藏了作品,没有一个拿出来卖掉的。”
尚陆认为,在国外,最早是博物馆、美术馆给一些摄影师举办展览,从而形成关于摄影的艺术观念,而最早收藏他们作品的就是美术馆和博物馆。摄影作品的艺术价值、市场价值等由此而来。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国内也没有一个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像美国、法国、英国、瑞士、比利时等(这些国家都有著名的摄影博物馆)那样,有政策、有计划地展览并收藏影像作品,也没有馆长、策展人或者摄影部门来真正关注摄影。“在‘中国人发现世界了’的欢呼之外,中国人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摄影更感兴趣?如果连中国的摄影史都没有搞清楚搞什么外国摄影收藏?连原作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怎么组织原作展览?”
去年的连州摄影节上,策展人那日松的一番解释让人对目前的摄影收藏群体的构成感受到了些许希望。那日松曾经告诉《艺术评论》记者,摄影师任曙光的系列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的收藏者,基本都是三四十岁的青年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媒体行业中工作,他们的收藏目的十分单纯——发自内心的喜欢。5000元的价格并不拒人以千里之外,或许因为这些与自身经历的中学时代十分相似的中学生形象,年轻的藏家们以此为门槛,踏入摄影收藏领域,这是摄影收藏的目标群体也是终极目标,对于艺术的热爱,而不是金钱的推动力。

辛迪·雪曼《无题第96号》,2011年5月纽约佳士得拍得389.05万美元。
艺术收藏如何回归到对于人文信仰和其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性、创造性的追问,而不仅仅是对于金钱收益的追求?在当下的中国,这是无论哪个门类的艺术收藏都面临的困境。前文中所提及的年轻藏家方喻,随着其藏品渐渐丰盛起来,对于他而言,更多的是一个精神财富的积累,而较少经济谋利的考虑。以同样的价钱介入艺术品收藏领域,有可能买到诞生于19世纪末的其他艺术品吗?方喻的答案是“难”。尽管一些收藏摄影的圈中朋友提供过通过一些可能谋利的项目——比如收藏了一个年代的摄影作品,向需要展出的方面出借,收取一定的借展费;比如出版社需要出版的时候收取一定的版权费。只要摄影市场不在几年内突然疯狂起来,方喻的目标不难实现,这也是一个年轻的藏家的心愿,“现在看起来一切似乎还好。”
但作为摄影的研究者,沪上摄影评论家顾铮对于摄影收藏话题并不持乐观态度,“用拍卖的方式无法做好摄影。普遍存在投机心理的藏家并不是真正热爱摄影的人。”当代艺术市场经历了狂飙之后,泡沫渐次破裂,也许只有挤干了泡沫,利益驱动的卡车刹车之后,剩下的用热情和真正的热爱支持着的收藏者才是摄影收藏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