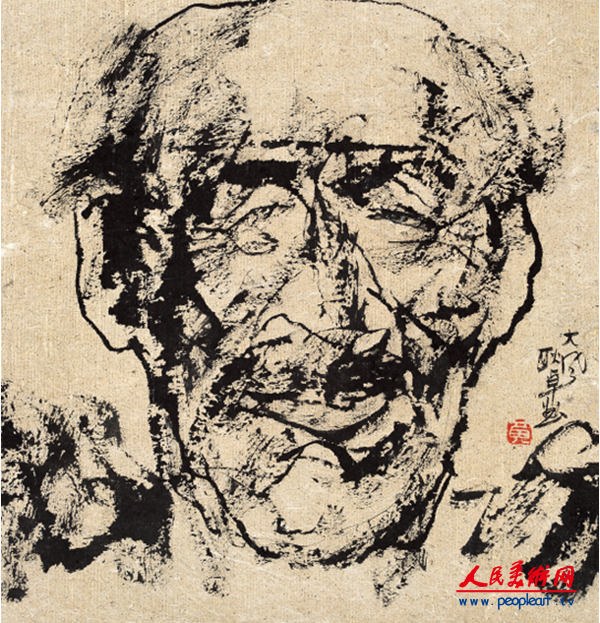
山村夜,宁静、昏暗,我被一阵悲凉的唢呐声吸引,走进了一座石屋。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蹲在板凳上吹着。屋里凌乱、阴冷,墙上帖了一排花花绿绿、含情脉脉或甜美微笑的美人图。桌上放着一个碗,一双筷。悲凉的唢呐声和满墙的美人图混在一起,是一种无需言状的凄苦。他给我倒水,我给他点烟。他说:十几岁父母先后去世,他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十年来,他盖了两处房子,给两个弟弟取了媳妇,嫁了妹妹,自己却荒过去了。他说的很平静,我的心却被打动了,诚心的说:“你是个好哥哥,你当了一个好‘父亲’”。这个汉子哭了,抓起唢呐用劲的吹了起来,他吹:大登殿、百鸟朝凤、得将令、小寡妇上坟……眼泪不时地从他那紧闭的眼睛中流出来。唢呐声激昂有力,委婉动人,如泣如诉。石屋里装不下那高亢的唢呐声,它冲出屋去,在山村的夜空中回荡……
我看过很多大乐团的演出,乐声再没有那样狠狠的揪过我的心。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山村的夜晚。
太行山给了我太多太多。
我爱太行山,我爱太行山上的人们。
我站在山坡上大声喊:“呵,呵,呵——”太行山也冲着我:“呵,呵,呵——”
太行山听见了我的声音,太行山听懂了我的呼唤。
黄耿卓
19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