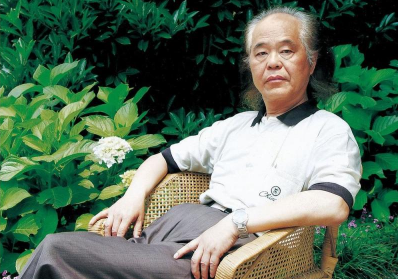
李敬仕
李敬仕:一个艺术爱好者的情感判断
傅雷知识宏富,学养精深,除了翻译和著述之外,还发表了不少评画言论,其中不乏富有睿智的远见卓识,被许多人叫好和热捧。但仔细推敲他的这些言论,其中存在的情绪性偏颇的荒谬之处也显而易见。作为一个评画者,傅雷首先是位艺术的爱好者和欣赏者。欣赏活动的特点,表现为一种感觉和理解、感情与认识的统一。其中,感觉和感情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艺术欣赏虽和艺术批评有密切联系,但两者在性质上又有显著区别。王朝闻指出:“艺术欣赏是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感受,艺术批评应当是对艺术作品进行逻辑思维的科学判断……通过一定的理论分析,对艺术作品客观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作出评价。”因此,作为学术研究活动的艺术评论,其价值观是中立的,即必须摒弃和超越个人的情感好恶,而采取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也就是说,艺术欣赏允许偏爱,艺术批评则要力求客观公允。傅雷为人桀骜不驯,秉性耿直而又嫉恶如仇,这使他评画时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因此,他的评论还仅仅停留在艺术欣赏层面而未进入艺术批评的层次,至多只是一个艺术爱好者的情感判断而已。
首先,从傅雷关于中国画的论述来看,他所钟情和褒扬的是文人写意这一风格的画。即使提及唐、宋,也是指王维、董源这类所谓“南宗”画家的祖师爷。否则,就是“甜熟”“恶俗”,是“画匠”“画工”。在这一点上,他和黄宾虹可谓情投意合。据画家陈佩秋回忆,她在上海美校读书时负责保管老师黄宾虹的画稿,同学们要临摹的话就到她那里去借,她发现同学们一临就像,包括她自己。对此,陈佩秋感到不满足。后来,她遵照另外一位老师郑午昌的建议,找了自己喜欢的五代画家赵幹的作品《江行初雪图》来临摹。她画了一个多星期,被黄宾虹看见了,就责问道:“怎么画这个东西?这是匠人画的。”但陈佩秋心里却认为:“文人画没有匠人画细致,匠人画要比文人画难画。”正是傅、黄的艺术观点的相同,即使年龄差距甚大,两人仍一见如故,引为知己。二人频通书札一百余件,惺惺惜惺惺,互为赏识。关于傅雷的评论,黄宾虹称“名论高识,钦佩无已”;傅雷则赞誉黄宾虹“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各家之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他能用一种全新的笔法给你荆浩、关仝、范宽的精神气概,或者是子久、云林、山樵的意境”,可谓是推崇备至。傅雷又说:“他(黄宾虹)的写实本领,不用说国画中几百年来无人可比,即赫赫有名的国内几位洋画家也难与比肩。”这种过甚其词的言说,不免令人掩口而笑。黄宾虹的画是经傅雷发现并推介的。他对黄宾虹的作品几乎没有提过一点意见,而且也不准别人发表不同看法。据说,施蛰存认为黄宾虹晚年因视力欠佳,其画越来越像个“墨猪”。此话一出即引起傅雷的大怒,批评施氏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画。另一方面,傅雷对以从画之大法出发,以塑造形象为核心的画进行贬斥。他指责张大千:“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何谓“外形为重”,何谓“唐人精神”,他没有明言细说。而我们所知道的张大千,其画筑基深厚,艺术业绩、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其对于工笔、写意,人物、山水、花鸟、草虫并臻佳妙,是位不可多得的全面型丹青高手。
其次,傅雷评画毫不忌讳地表现出一种浓重的感情色彩,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必要否定其画。批评标准应该是根据一定的社会思想和美学观点提出的。它必须适应一定历史时期广大群众的欣赏需要、审美趣味以及文艺发展的需要,而不是随着评论家的喜恶可以随心所欲改变的。傅雷对刘海粟的评价,却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矛盾现象。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和刘海粟交谊甚笃,有段“蜜月”时期。那时,他写了《刘海粟》一文,里面写道:“……愿你,海粟,愿你火一般的颜色燃起我们将死的心灵,愿你狂飙般的节奏唤醒我们奄奄欲绝的灵魂。”又,“一个真实的天才”,“我只问中国要不要海粟这样一个人”。这样高调的称颂几同肉麻的吹捧。回国后,傅雷因为看不惯刘海粟的所作所为,两人开始交恶乃至绝交。刘海粟的画也就在傅雷的眼中成了“从未下过真功夫而但凭秃笔横扫,以剑拔弩张为雄浑有力者,直是自欺欺人……鄙见只觉其满纸浮夸(如其为人),虚张声势而已……他的用笔没一笔经得起磨勘,用墨也全未懂得墨分五彩”。又如,他因看不惯张大千善于借势结交权贵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对他举办展览卖画,画价定得太高就愤愤不平,责备他“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吴湖帆率门人开画会推销作品,也受到傅雷的猛批:“……作品类多,甜熟趋时,上焉者整齐精工,模仿形似;下焉者五色杂陈,难免恶俗矣。此教授为生徒鬻画,计固良得,但去艺术远矣。”在傅雷看来,中国画走向市场,辱没了文人的尊严,必然江湖气十足,难免恶俗。
再次,是对人物画的忽视和贬低。面对当时卓有成就的徐悲鸿、蒋兆和等画家的人物画,他几乎视若无睹,不置一词。对于造型能力要求较高的人物画(特别是肖像画),文人们是难以涉足并忽悠大众的,所以以保持沉默为佳。即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或以“俗气”加以否定。傅雷在提及张大千的人物画时,批其“创作往往俗不可耐,仕女尤其如此”,又批徐燕孙“在此开会,标价奇昂(三四千者触目皆是),而成绩不恶,但满场皆如月份牌美女,令人作呕”。
本来,评画应该从画之本身优劣出发。譬如《清明上河图》被公认为中国画的经典作品,是因为这幅画的艺术水平令人叹为观止,并没有人去追究作者张择端的人品是优异或有瑕疵。傅雷则是从“画以人传”的思维出发,把道德置于画之上,把他看不惯的画家打入谷底。这样的评论类似戏剧界的票友,执拗地为了自己所心仪的演员,不惜和其他演员的粉丝发生冲突,甚至大打出手。所以,他的画评基本上还停留在直觉状态的个人体验和感悟,甚至超出了作品本身的范围,借以宣泄个人的好恶和情思。因此,对于这样的画评,我们可以作为参考,但不必当真,否则自己也会掉入情绪偏激和偏听、偏信的泥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