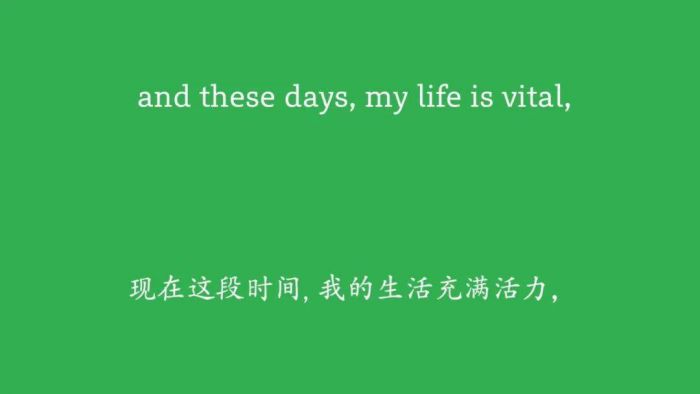
赵要,《有神的信号 - 抑郁症,我们分享的秘密》截屏,2018.
“梦饮酒者”似乎在寻找传达这一危机的方式,策展人也似乎有意地对这一封闭的媒介空间中的生存姿态进行了融合:旋转对于注意力的捕捉(陈天灼,《拉西亚》)、私人空间中的亚空间跃迁(《我们俩:游戏漫游》)、第一人称视角的切割(《How to Slay a Demon》)、匀速行进的数码有机体(《内存腐蚀》)……假如普遍性(哲学与科学)与个体性(艺术与经验)不再被肉身的我们所中介,这样的世界是可以承受的么?在“梦饮酒者”的终章(赵要,《有神的信号》),被之前所有作品消耗得精疲力竭的我,舒适地读完(听完以及看完)了所有字句。这样的字句或者说信号,也会遵循“黑暗森林”法则,被某种对抑郁症怀有敌意的存在所抹杀么?不,也许更为糟糕,由于“不可退出”的社会机制不再有一个可被想象的外部,即使是一种值得时刻警戒的鲜活的外部威胁都是不可得的,当下时代的威胁更多地来自于内部,也湮灭于内部。这也是新媒介潜藏的暴力所在:被时刻上传,而又时刻无法上传或表达。
当艺术力图拆除“第四堵墙”,以便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时,这面墙到底是被摧毁了还是被重置了?在被作为拆迁补偿的反思判断力失去了现实连接之后,我们又何尝不处于“成为墙”这件事本身的诱惑之中?也许在经典美学家那里被承诺为反思判断力的东西,在新媒体艺术家及其策展中应被转为一种穷竭一切的行动力。就像《内存腐蚀》中行走的躯体,却需要一种更快的匀速……
比如想象自己是一道光,只遵循最基本的光学原理,被不断的折射与反射,直到探明所有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