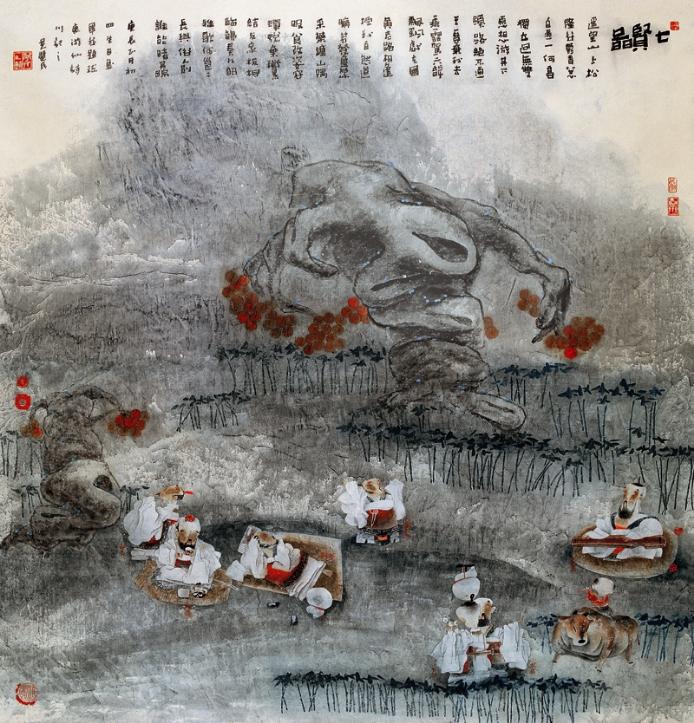
視覺上的簡化,首先要對物象進行提煉。這種提煉以扎實的課堂與現場寫生和光影素描為基礎,但他並沒有循此路數發展下去(發展下去的結果是成為第二個葉淺予、黃胄、周思聰......唯獨不能成為他自己),而把汲取靈感的範圍擴大到幾個相隔甚遠的領域——漫畫的誇張與黑色幽默、漢畫簡化的塊狀感與黑白對比,甚至岩畫和世界範圍內的“原始藝術”的造型與符號。漫畫和漢畫是中國繪畫的邊緣,但並非與水墨畫傳統絕緣,而岩畫和原始藝術則已被吸納為西方現代藝術的元素,對它們的利用也是中國畫形式現代化的一種路徑。為了與畫面造型與氣質相符,他的書法也取法有民間淵源的魏碑字,主體來自龍門造像記,相容“二璺”,字形和用筆都方正古拙,勁力內含,與他的自署“醜人”相得益彰。
畫面的簡化與平面設計感的加強是他最近10年創作上的另一個大變化。在有題跋的創作中,題跋作為畫面的結構元素,或縱長,或橫列,突出形式感。如《高空有月千山照》的題跋兩字一行,一共10行,橫列於畫面中下部,像隱士背後的地面。《無語聽天》畫的是橫臥的大頭像,人物雙目圓睜,眼神空洞,不像處在休息中,倒像是被斬下來的腦袋,畫面在上、窮款在下,也是作橫式處理。《晚秋圖》、《徐文長造像》和《臉上遊戲》的題跋皆為縱長一整行。1994年(甲戌)所作隱士四屏之一《獨釣》則為縱長雙行,畫面上只有一個釣夫、二遊魚,其餘是整片的空白,極端的對比,令人驚心,兩行題跋有如一柱擎天,險中求穩。1997年的《嚴重時刻》是這類設計的頂峰,中間是一個大頭像,貼著畫面的兩邊是兩行細長的題跋字跡。到後來,許多大頭像畫法愈益簡化,題跋也變成了畫面一側或是兩側的縱長線條,或粗或細,或單或雙,或勾或抹,其意不可說,充滿神秘感。最後,許多大頭像的背景乾脆變成了完全的空白,只看到一顆腦袋和細長的脖子,有如高高舉起的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