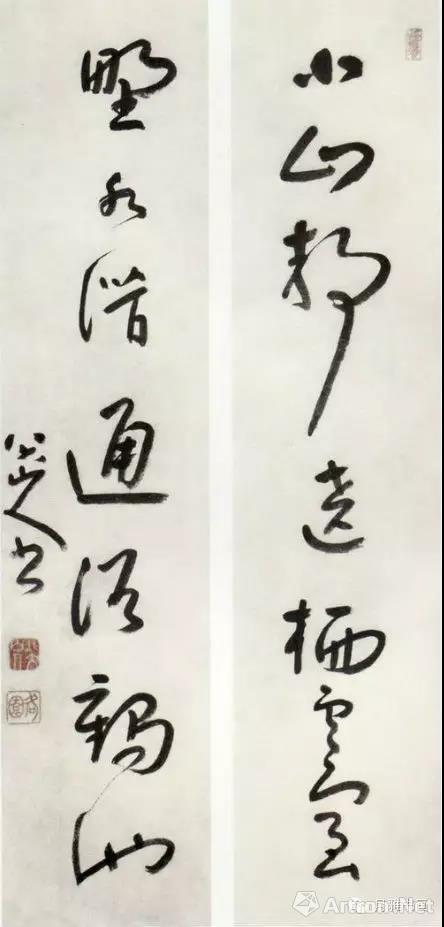
我们比较一下八大山人晚年书于前后两个不同时期但内容相同的两幅作品。两幅作品均为《送李愿师盘谷序》轴。第一幅署款“?大山人”形(图七),应为山人晚年前期的作品。第二幅署款“八大山人”形(图八),应为晚年后期的作品。从字形幅式来看,两幅作品的书写时间相距不会很长。作于晚年后期的那一幅作品,刘墨认为“按署款方式,此似应作于74岁左右”,并认为是八大山人的代表性作品。笔者以为,作品时间应在74岁往前靠,----时八大山人64至65岁)后写《八大山人传》称八大山人“狂草颇怪伟”。从八大这一时期所存作品来看,称其倾向于图案的“画字”书风为“怪伟”,的确是比较贴切的概括。这一时期持续不长,69岁以后八大山人的书风逐渐倾向于端庄平和,章法变知己石铺地、参差错落为竖势排列,少夸张之态。故本节所举后期的那幅作品,正是较多地保留有前者的形态,又有后期某些特征的过渡性作品。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其艺术营养是来自多方面的,反映在作品中,艺术面貌也是丰富多彩的。合刊于《中国书法全集》第64卷里有八大山人《致鹿村等十三札》(图九),署“?大山人”款形有十札;署“八大山人”款形有三札。该卷编者刘墨有评语说:“十三札同属八大山人的晚期作品,但时期却有差异,书体也多样化。其中十札款署‘?大山人’形的款,当作于山人64至69岁之间。其余三札署作“八”形的款,证明是山人80岁时作。”署“?”形款十札的书法风格近黄道周书风,字形略扁,线条圆劲但少涩感,章法介乎参差错落向竖势排列过渡之间,结字间杂有图案化之“怪伟”字出现,如“画”、“鼐”等字。署款为“八”形的三札,章法全为竖势,线条浑厚涩迟,点画出锋含蓄,结字端庄,帖学意味甚浓,无怪伟之象,书风受恶唐及董其昌影响明显,图案化现象全部消失,为晚年后期返朴归真时的代表作品。
八大山人晚年两个不同时期书风的变化还反映在他数幅临王羲之《兰亭序》里。这里我们拈出两幅予以比较。一幅署“?”形款,跋尾有“癸酉五月廿日更临一过”语,可知作于68岁,系晚年前期作品(图十)。另一幅署“八”形款未纪年,但被装于同册的有《东坡居士游庐山记》一幅,跋尾谓“庚辰之夏日漫之”,从款形及风格可推知,后一幅《临兰亭序》作于75岁,是山人晚年后期的作品(图十一)。众所周知,八大山人《临兰亭序》纯出己意,于原作相距甚远。在不同时期用自己那一时期惯用的某种风格书写同一内容的作品,在这两幅《临兰亭序》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三
不同时期的书法风格,反映出八大山人不同时期的生存景况、心理状态和艺术思想。邵长蘅在八大山人64岁时与之面悟后描述当时他的情态:“山人胸次汩渤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如湿絮之遏火,无可如何,乃忽狂忽暗,隐约玩世,而或目之曰狂士,高人。”八大山人于康熙十九年(1680)55岁佯狂由僧还俗后,心情如“巨石窒泉,湿絮遏火”,一腔愤懑,无从发泄,倾之于书画,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忽狂所暗扭曲之心态转换为变形之“怪伟”书风,足以惊世骇俗!
八大山人晚年前期书风呈“怪伟”状,亦与禅宗、道教有关。八大山人于顺治五年(1648)23岁时剃发为僧,一度开堂说法,浸染禅学甚深,为著名高僧。其后跋画诗也常用禅语。清人龙科室说他“题跋多奇慧不甚可解”。大约指的就是八大山人多用隐讳的禅语表达内心隐痛的缘故。明代禅学常以老庄释禅,“狂禅”之风不减,连儒学大师王阳明也受其影响,写出了比之于释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不衫不履之诗:“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得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其主旨是提倡人之主体精神,有蔑视权威的倾向,这是明中叶以后的社会思潮。八大山人在《个山小像》上有这样一首题诗:“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曹洞临济两俱非,赢赢然若丧家之狗。还识得此人么,罗汉到底!”。按:宋吕萧《如净祥语录序》说:“曹洞机关不露,临济棒喝分明”。曹洞,临济两宗均为禅宗之极慧黠者,极具个性者。山人为僧,先入曹洞,后又入临济,两宗兼习,禅学的隐藏与机锋对山人的修炼与其“怪伟”的书风相为表里。